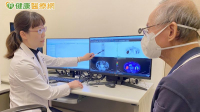一、沒有規則可循-做「你」需要做的事
意外事件發生以後,特雷弗和我都很清楚,我們不必遵循任何規則。傳聞湯瑪斯.艾爾發.愛迪生(Thomas A. Edison)說:「這裡沒有規則,我們正在努力完成某件事情。」一旦某件事和生存同樣重要時,生活常規就不適用了。你人就坐在駕駛座,你是最重要的,你得去求生存。你有絕對的自由權,做什麼都行,只要能熬過最初的幾天和幾週即可。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感受什麼就感受什麼,沒有人可以命令你。
就在艾比死後的最初幾個小時和幾天裡,我突然發現只對自己負責是多麼重要。我身為母親,失去了愛女,早已天塌地崩,我有權去決定自己想幹什麼事。我每遇到一件事情,都會問自己:「這能夠幫我們度過難關,還是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當我們決定是否要去法庭看闖禍司機的審判時,我們會從長遠的角度來想:這樣是否有助於我們熬過悲傷的日子(因為我們會覺得要還艾比公道)? 或者我們坐在法庭,看著這個傢伙被質詢,同時重溫那些「如果當初怎樣,結果就會如何」的時刻,是否會讓我們眼下和未來更難熬。透過這種方式去看待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詢問自己:「這會幫助或傷害我 ?」)是認知行為療法的核心原則。我在賓州大學的復原力課堂中首次聽到這種觀點,我現在發現它是一種比社會習俗更能用來評價世界的標準。別人都認為我們會出庭,但我們不需要這樣做。出庭無法幫助我們,只會讓我們再次受傷。
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我認為走自己路有時並不容易。我知道社會對我的期望,也知道先例是什麼,但我認為自己非得選擇不同的道路。我不是在談論重大的違規行為,而是談論某些微小的抉擇,好比決定不打開我們每天收到關懷來信。我想以後再看這些信,這樣可能會讓我感到慰藉(譬如當我需要聆聽關於艾比的新回憶時,甚至在我的腦海強化她已經離世的事實時),我保留了一些信件,不去拆封。雖然有人會認為不打開他們寫的信很不禮貌,但我此時選擇把自己的需要擺在首位,只做對我有益的事。我基於同樣的理由,甚至不會給所有送花和送餐的人回信,我真的很感謝他們,但一一回信實在會加重我的負擔。
同樣地,我感到非常驚訝,許多父母和配偶痛失親人以後,竟然願意接受媒體採訪,搞得自己精疲力盡,但這樣顯然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大家聽著(艾比會這樣說),沒有人有權在你受到重創以後立即採訪你,因為你飽受震驚,還無法仔細思考。如果你想接受採訪,那就去做,但假使你真的不想,或者你還不確定,那就拒絕受訪。如果你有想說的話,以後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發表意見。
我們要詢問自己「這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或者會妨礙我們復原」,以此來質疑我們的想法和行為,讓我們飄浮在無助的海洋之際,能夠獲取一丁點掌控權。
二、選擇你要關注的地方
人處理事情的能力有限,我們的能力絕非無窮無盡。
如果我告訴你,人腦大約只有一五○○立方公分的處理能力,你可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假使我改口說,根據科學家的估計,人在任何時候只能處理七個位元(bit)的訊息(亦即區分聲音、視覺刺激、解碼情緒和思想),你可能就比較了解我所說的話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很難去理解這些數字對我們可憐的悲傷心靈所帶來的影響。各位要理解的重點是,人腦即便運作正常,處理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允許哪些訊息進入我們的意識便非常重要),所以對於哀傷的人來說,選擇正確的材料(訊息)將有多麼重要。在艾比死後的幾天、幾週、甚至幾個月以內,我的大腦絕對不會處於最佳的運作狀態。
傳奇的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yl Csikszentmihalyi)說道,如果我們可以體驗的事物是有限的,將注意力集中在什麼東西上就會深切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內容和質量。我了解這一點之後,便知道不要將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浪費」在指責撞死艾比的那位司機。根據我接受的訓練,那樣做是有礙復原力的思維,我們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桑迪.福克斯(Sandy Fox)的二十七歲女兒和獨生子被人開車撞死,結果那人卻肇事逃逸,而桑迪採取的態度也跟我非常相似。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撞她車子的貨車司機一轉眼就不見了。他肇事逃逸以後,消失無蹤,再也找不到了。朋友們問我:『他逃掉了,可以不受懲罰,難道妳不生氣嗎 ?』我仔細想了一下,最後下定決心:『不,我不想坐在法庭上,聽到他重述肇事過程,也不想看著他的眼睛,永遠記住他的臉。』我這樣好受多了,不必再經歷那件事,也不必再一直做噩夢。」
桑迪選擇不去追捕司機,因為她不想悲傷時還得記住這個人的面容,這樣她才會「好受多了」。
我一直認為,肇事司機在我的家庭悲劇中只是個「小角色」。契克森米哈伊的建議是,我們如何過生活(有何種形式和內容),取決於我們如何引導我們有限的注意力。事故發生後的最初幾個月裡,我一直想著這項建議。契克森米哈伊寫道:「你如何投入精力,就會衍生出截然不同的現實。」
如果在艾比去世前,我曾經聚焦過自己的注意力(想像成手電筒的光束,非常刻意聚焦在某一個地方),那麼在這個因悲傷而能量大幅耗盡的新世界裡,我就決定不要將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無意義的地方。
別忘了,你可以自行選擇要將生活的注意力集中在何處(你也要知道自己處理外部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這是特別強大的工具,在經歷喪親之痛時可以運用。你可以選擇將光束聚焦在什麼上。要怎麼做,由你決定,不要受你的父母、朋友、媒體、律師、恐怖分子、司機,甚至關注受害者的人士所影響。我女兒死後,凱倫.瑞維琪給我捎了訊息,指出復原力「是讓你刻意將注意力放在對的地方」。
三、慢慢來
艾比死後的隔天早上,我兒子的學校牧師博斯科.彼得斯(Bosco Peters)和他的妻子海倫來拜訪我們。我大概得知博斯科的女兒凱瑟琳也是發生意外而喪生,但我記得自己當時因為覺得不好意思而不敢過問,以免問錯了失禮。到了星期天,牧師和海倫又來拜訪我們,我們和他們一起坐在客廳喝茶聊天,在場還有其他人。他們說凱瑟琳死後,他們悲傷了五年,過得悲慘痛苦,然後給了我們一些不錯的建議。博斯科說道:「別著急,慢慢來,這幾天什麼都別急。你們要慢慢適應艾比已經離開。如果還沒準備好,就不要急著舉行葬禮。你們有的是時間。」
他們從旁支持我們,分享他們來之不易的寶貴經驗,讓我真的心懷感謝。他們知道,一旦死者真正離去(無論土葬或火葬),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去哀悼他們。艾比星期六去世,禮儀師整理好遺體,星期三才把她送回家。多虧了博斯科的建議,在下週一的葬禮之前,我們有五天的寶貴時間可以陪伴艾比。
我在家陪伴艾比遺體的那段時間,不僅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我悲傷的方式。這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儀式,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知道這對別人也很重要。金伯莉(Kimberley)是我的密友,他的兒子亨利(Henry)是艾比和艾拉最親密的朋友,而我最近從金伯莉那裡得到了一條短訊,正好提醒我讓艾比回家並與她共度時光有多麼重要。「謝謝你讓我們和艾比共處。昨天過得很棒,我們跟她說了再見以後,內心感到更平靜了。我希望今天和你的女兒在一起時能讓你感到寬慰。如果你想要別人給你打氣,隨時來找我們。」

本文摘選自《悲傷復原力》,采實文化出版。